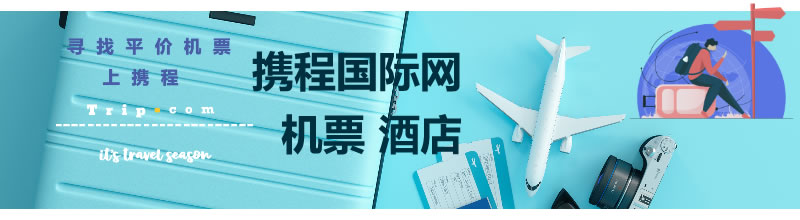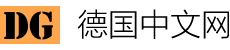“秘密报告”引风波,德情报机关将AfD定性为极右翼引发质疑

德国宪法保护局近日一份关于德国选择党(AfD)的评估报告引发广泛争议。这份耗时数年、长达1100页的内部文件将AfD正式定性为“确认为极右翼势力”,指控其违反人的尊严、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然而,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结论本身,更在于报告几乎完全依赖公开资料,缺乏情报机关应具备的独立信息来源。
报告的依据主要来自AfD公开发布的纲领文件、网站内容、社交媒体发言以及在集会和选举演讲中的言论。甚至一些网络平台X上的“表情包”也被引用在内。德国知名“抄袭猎人”韦伯批评称,整份报告更像是一份堆砌的引文合集,部分段落直接摘录自与AfD无关的法庭判决文本。他质疑道:“这样的内容真的需要一个情报机构来撰写吗?”
尽管报告主要依赖公开信息,却仍被列为“仅供内部使用”的保密文件。前内政部长南希·费瑟(SPD)在卸任前坚决反对公开发布该报告,理由是“为保护信息来源”。不过舆论普遍质疑,这样的文件中究竟有哪些信息需要保护?为何不能以技术手段删节敏感部分后公布?
宪法学者赫贝图斯·格尔斯多夫(Hubertus Gersdorf)批评称,这一做法是对民主透明原则的严重破坏。他表示:“公民有权了解这样一份对国家政治格局有重要影响的报告内容。”他认为,报告理应公开,哪怕是以删节版形式。
媒体《Cicero》近日率先曝光了部分内容,引发社会各界对宪法保护局评估机制的质疑。许多人认为,如果AfD的问题仅通过公开信息即可识别,是否还需要一个情报机构来重复性整理这些内容?更何况,报告中使用的“确认为极右翼”一词,在德国《宪法保护法》中并未明确定义,在法律和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解读。
宪法专家沃尔克·伯梅-内斯勒指出,该术语在法律中缺乏精确定义,将其用于党派评估存在极大模糊空间。而一旦该术语被广泛使用,其他组织也可能以此为由,要求政府公开更多类似报告,进一步挑战宪法保护局的边界。
人权律师兼言论自由倡导者罗尔夫·格斯纳(Rolf Gössner)则认为,该报告并不具备不可替代性。媒体与研究机构多年来持续关注AfD,其民族主义、排外言论早已广为人知。他表示:“我们并不需要一个秘密机构来告诉我们AfD在推动怎样的意识形态。”
他还指出,AfD长期鼓吹“再迁徙”等排外口号,与新纳粹势力有明确联系,其煽动性言论也导致德国右翼暴力事件不断上升。他质疑:“难道我们应对这些社会风险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情报系统出具‘官方认证’?”
格斯纳曾因与左翼组织有接触而被宪法保护局长期监控。2020年,联邦行政法院裁定对其的监控侵犯基本权利。他获得了约2000页档案,但其中80%被涂黑。他讽刺道:“在AfD报告的保密处理上,情报机关显然没有这么‘细致’。”
尽管这份报告本身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格斯纳指出,这一“贴标签”行为严重影响AfD作为政党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参政自由和平等竞争权。更令人担忧的是,AfD在报告公布前并未获得任何申辩机会,这从法治角度看极具争议。
此外,宪法保护局的《年度报告》也存在类似问题,其经常在未经审判程序的情况下,将个人或组织列为“极端分子”或“宪法敌人”,却不给予任何辩护机会。
此次围绕AfD报告的争议,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政党与情报机关的对抗,而是触及德国民主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如何确保政治透明、公正和法治?而宪法保护局在这一结构性张力中的角色,或许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