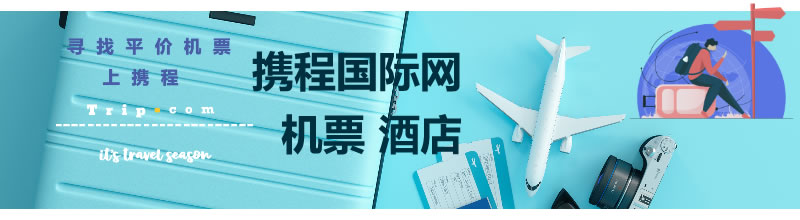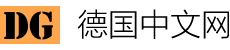德国将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引发社会全面军事化转型

在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和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相继宣布将大幅扩充军力后,德国正站在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门槛上。联邦政府提出,计划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使德国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成为“欧洲最强的常规军”,并意图在北约内部扮演军事领导角色。这一决定标志着德国自1990年统一以来最剧烈的社会结构转变之一。
梅尔茨在上周的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重建德国军力是新政府的“绝对优先事项”,并承诺将为此“提供一切必要资金”。他宣称,德国的盟友几乎是“迫切希望”德国在欧洲承担领导责任,并强调这一目标不仅出于防务需要,也是德国对外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所在。梅尔茨指出,德国的全球影响力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因此德国也要成为世界“引人注目的增长引擎”。
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则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期间详细阐述了这项计划。他表示,德国将全面支持北约未来将成员国军费标准提升至GDP 5%的目标,并称德国“准备好,也有能力”将国防预算增加至当前的两倍半左右。根据规划,未来将有3.5%的GDP直接用于联邦国防军,另1.5%用于军事基础设施。这将使军事开支在德国联邦预算中的比重超越社会保障与养老金等传统最大支出项。
如果该计划全面实施,德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将高达1500亿欧元,另有650亿欧元用于军事基础建设。瓦德富尔强调,德国不仅愿意承担领导责任,还将鼓励其他国家“效仿德国的榜样”。
从财政角度来看,这一雄心勃勃的军备计划极可能使德国在欧洲军事格局中超越法国与英国。相比之下,法国与英国的公共债务已接近GDP的100%以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法国债务占GDP比重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116.3%,英国也达103.9%。这限制了两国实施类似德国那样债务驱动型军备扩张的能力。因此,德国几乎已扫清财政障碍,为其成为“欧洲第一军事强国”铺平了道路。
然而,这一政策方向也引发了德国国内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尽管德国汽车工业仍占GDP的约5%,但其产能正在萎缩。据德意志银行研究报告,自2011年以来,汽车产量已下滑31%,大众和福特部分工厂的产能利用率甚至低至25%-35%。相比之下,军工产业虽然目前仅占GDP的0.2%,却正迅速增长。报告建议,应加速将汽车工厂转型为武器装备生产线,以快速建立军工产能,并推动军工企业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大幅上升。
随之而来的,是德国社会日益明显的军事化趋势。一方面,医院等传统民用机构正被纳入战时预案中。据估计,若爆发战争,德军每日可能出现约1000名伤员,因此医疗系统正被要求将“战争准备”作为优先任务。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也正面临增强“战时抗压能力”的压力——政府建议民众囤积物资,并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准备。
在社会舆论层面,德国主流媒体已开始公开呼吁“增强牺牲精神”。《法兰克福汇报》近期撰文称,“所有伟大的文化成就都依赖于个人和集体的献身意愿”,“集体的牺牲勇气”应被视为未来防御的关键资源,值得广泛培育。
尽管社会仍对全面战争保持警惕,但根据最新民调,已有50%的德国人支持让德国“具备战争能力”,仅有31%反对。不过,真正表示愿意“为德国而战”的人仅占29%,有54%的民众仍明确拒绝亲自参战。
德国正在经历一次深远的军政转型。在梅尔茨政府推动下,德国正逐步告别“战后克制”,迈向一个以军备扩张、战略自主与大国领导为核心的新阶段。这不仅意味着德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将扮演更具主导性的角色,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军事共和国德国”正悄然成形。